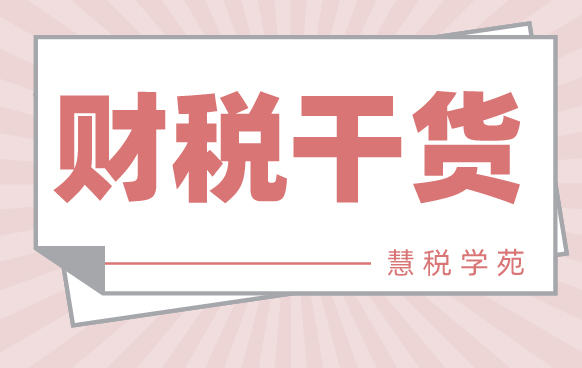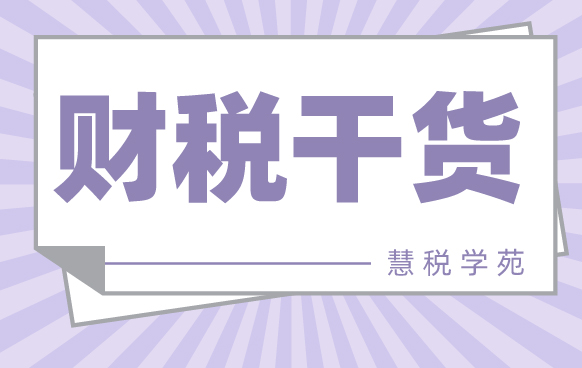海外税收案例四十三:关注非居民间接股权转让免税政策适用性问题
一、案例简介
新加坡A公司在新加坡投资成立B公司,B公司投资印度C公司,取得部分股权。2014-2015财年,A公司将其持有的B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印度D公司。A公司认为,该交易虽然涉及间接转让印度C公司财产,但根据印度所得税法关于间接财产转让小股东豁免规定,无需在印度纳税。
印度税务局则认为,间接财产转让小股东豁免条款自2015-2016财年起生效,因此上述交易不能适用豁免规定,应在印度缴税。其后,A公司向印度争议解决小组(Dispute Resolution Panel,DRP,是根据印度所得税法引入的法定机构,由印度中央直接税管理局任命,为外国公司或特定国内纳税人提供快速、中立的争议解决机制,避免直接诉诸所得税上诉法庭,减少诉讼积压并提升税收确定性。)提出反对意见,但被其驳回,理由为:印度“所得税法没有明确规定小股东豁免可以追溯适用”。最终,A公司向新德里所得税上诉法庭提出上诉,法庭支持了A公司主张。
二、争议焦点
本案中,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新加坡A公司转让新加坡B公司股权取得的收益是否适用间接转让小股东豁免条款。
新加坡A公司主张:一是在适用条件上,印度《2012年财政法》条款5和《2015年财政法》条款6、7(相关法律规定网站:https://www.incometaxindia.gov.in)对《1961年所得税法》第9节间接财产转让进行了解释。
相关条款具体内容如下:条款5:非居民转让外国实体的任何股份或权益,如果该股份或权益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印度资产,则所产生的收入应在印度纳税。条款6:如果境外企业持有印度公司或实体股份少于5%,则享有小股东豁免权。条款7:境外企业持有的印度资产价值超过1亿卢比,且至少占该境外企业资产总价值50%以上时,印度有征税权。
A公司的相关交易符合间接转让小股东豁免规定。
二是在适用时间上,印度《2012年财政法》明确,条款5可按规定追溯至1961年4月1日,《2015年财政法》虽未明确条款6、7可以追溯适用,但由于条款6、7是条款5的补充说明,也应追溯适用至1961年4月1日。
因此,该交易可以适用间接股权转让小股东豁免规定,不需要在印度纳税。
印度税务局则认为,正因为条款6、7 是《2015年财政法》引入的,所以豁免规定应从2015-2016财年开始生效,而不适用于该笔间接转让发生年度,即2014-2015财年。
三、最终裁决
最终,新德里所得税上诉法庭裁决A公司胜诉。主要理由为:
条款5由《2012年财政法》引入,并可按规定追溯至1961年4月1日。在引入该条款后,有人针对其中“任何股份或权益”和 “主要”一词的模糊性向印度政府提出了申述。印度政府将申述意见提交专家委员会,由其研究提出明确间接转让可税范围的建议。此后,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,印度通过《2015年财政法》引入了条款6、7。因此,根据立法本意,条款6即“小股东豁免规则”和条款7即“主要价值测试规则”应与条款5一并追溯至1961年适用。
因此,纳税人有权就2014-2015财年发生的间接转让适用小股东豁免条款。
四、对“走出去”企业的启示
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可能采用与上述案例相似的股权架构,因此在发生企业集团架构变化时,或面临类似的间接转让税收风险问题,应对此予以重视。
一是关注东道国税收政策与税改进展。“走出去”企业在搭建海外架构之前,应充分了解当地税收政策。例如,印度自“沃达丰案”之后对于《所得税法》进行了多次修正和解释,尤其是资产收益税方面。企业应及时跟进最新政策,针对与企业密切相关的部分提前与当地税务机关充分沟通。
二是预先考虑海外架构的退出成本。对于间接转让等投资退出时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,企业应熟悉相关判定和计算规则,如安全港规则、价值测试规则等,做好退出成本预判,同时还应密切关注东道国和相关国家税收协定相关条款的修订情况。
三是用好东道国税收争议解决机制。在遇到跨境税收争议时,“走出去”企业应多途径寻求税收救济。例如,对于印度资本收益税争议问题,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局的所得税上诉委员会(CITA)提出上诉。如纳税人对所得税上诉委员会的裁决不满意,还可向所得税上诉法庭(ITAT)提起上诉。除诉诸法律外,企业还可选择相对高效的替代性税收争议解决办法,如向争议解决专家组、所得税和解委员会等机构反馈诉求等。通过用足用好各类税收救济手段,合理有效维护自身权益。
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编译
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审校
相关推荐
-
告别“拖后补”:一文读懂新版《欠税公告办法》
后来已经把税款和滞纳金都补齐了,在公告内容中仍然可能保留“曾经发生欠税并产生滞纳金”的记录。实践中不少企业存在“先拖后补”的习惯,在新的制度环境下,“先拖一拖”的做法,合规成本已经远远不止滞纳金。
-
畅通市场退出与再生通道,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
日前,国家税务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《关于企业破产程序中若干税费征管事项的公告》(以下简称《公告》),对企业破产程序涉及的税费债权申报、征收管理、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等关键事项予以明确。
-
强化数据交换 严防“买单配票”
笔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,2021年至今,案件名称包含“骗取出口退税”的1918份判决书中,96%的案件按照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用于骗取出口退税、抵扣税款发票罪”定罪。